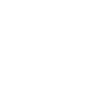2018年5月30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遼
銅佛板
高 24.7 cm (9 3/4 in)
保留價: HK$ 600,000 / RMB 480,000
這件銅佛板為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發現同材質最大的一件。
佛板通體採用模範鑄造而成,呈豎長方形,輪廓分明,圖像清晰。整體作單間殿堂式建築造型,原有兩葉木製對開門扇,出土時門扇已經不存。佛板上端為廡殿頂,用以代表佛殿的存在。正脊中央設置一刻有蓮花圖案的寶蓋,正脊兩端各設置一魚頭形鴟吻, 屋頂面作瓦壟狀,猶如寺廟大殿屋簷,簷牙上翹,屋簷下刻畫類斗拱裝飾,具有遼宋時期雕刻和建築藝術的鮮明特點。佛板身部四角各有一突出前方的穿孔附件,用於穿插兩扇門軸。佛板下方為長方形底座,底座上線刻寶相花紋。
巨大而立體的屋簷下是一幅立體感極強的淺浮雕佛畫。畫面主體為一佛、一弟子、一菩薩的三尊像,上方從屬擔負寶蓋的二飛天。主尊佛雙手伸展於胸前拇指相對並舉結印,面相飽滿方正,五官刻畫清晰,棱角分明,雙目微閉,大耳垂肩,頗具有陽剛之美,其造型風格與遼代同時期造像極為接近(參考遼代上京南塔之西北面下層的佛陀浮雕),反映了遼代草原民族的審美趣味。
中原北方初唐坐在蓮花上施轉法輪印的佛陀是作為阿彌陀佛表現的。 此佛板中雙手於胸前拇指相對並舉印相不屬於密教印相,最大可能就是轉法輪印的變通表現,類似情況所在多有,形成遼代佛教造像的一個典型特徵。如果這一推論能夠成立,那麼該主尊佛應為阿彌陀佛。
主尊阿彌陀佛下承蓮座屬典型遼代樣式,束腰大仰蓮,蓮瓣肥碩飽滿,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翹起,十分生動。這種盛開的仰蓮座在隋代以前所見不多,而大仰蓮座在宋遼時期最為流行,且花形飽滿,呈怒放狀。如延安子長鐘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為仰蓮座,大同華嚴寺及應縣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據子長鐘山石窟題記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所鑿,恰與應縣木塔遼清寧二年(1056年)始建時間大致相同,可知此種形式的蓮座曾廣泛流行於宋遼時代。
蓮座左右兩側之協侍分別為一弟子及一菩薩。左側弟子著垂領式袈裟,內側身跪坐,雙手合掌供養。右側菩薩盤腿坐在小蓮座上,頭飾花鬘,身佩瓔珞,側首仰望主尊阿彌陀佛。二協侍姿態、台座明顯有別, 這是製作者針對二者各自身份而有意設計的。右側協侍菩薩反映了其助佛教化的功能;左側協侍弟子跪坐合掌供養阿彌陀佛, 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遵從聖教,歡喜奉行,另一方面佛弟子身份近於一般人,似乎還隱含著引導芸芸眾生皈依阿彌陀佛的用意。自南北朝以來,阿彌陀佛通常以觀世音、大勢至菩薩為協侍,形成西方三聖組合,與西方淨土類經典記述一致。此佛板之阿彌陀佛協侍一弟子及一菩薩,這種不對稱組合在佛教造像中十分罕見, 這也是此佛板的特色之一。
主尊佛上方懸浮寶蓋,雙層蓋簷,周緣垂幔。主尊佛兩側分別浮雕一橢圓形雲團,每個雲團中各有一身飛天作合掌供養狀, 後肩擔負牽連寶蓋的繒帶。追本溯源, 這種不一般的造型其實關聯著犍陀羅和北魏的造像。少許犍陀羅成熟期的浮雕可見犍陀羅大神主尊上方有左右二飛天捧持花蓋供養。花蓋供養見於佛教經典,為南亞古老傳統,飛天捧持花蓋造型則是藝術家的創造性表現。類似二飛天捧持花蓋的藝術設計形式,於北魏中期(439—493 年)傳播到中原北方,用於當時流行的金銅佛板,如定州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銅佛像,表現為二飛天手牽連綴寶蓋的繒帶,由二飛天捧持花蓋轉變為二飛天捧持寶蓋, 這顯然是適應中土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結果。不難看出,該實例二飛天手牽連綴寶蓋的繒帶,與本佛板二飛天擔負牽連寶蓋繒帶的表現相差無幾,兩者應該存在傳承和發展關係。可以推斷此佛板在製作之時可能參考借鑒了傳世的北魏金銅佛板。
1977年內蒙古巴林左旗野豬溝鄉蓋家店村(位於遼上京城址附近)出土的一件遼代小型青銅佛板,現存於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形製與此拍品相似。兩者皆是佛殿式造型,主尊阿彌陀佛均協侍一弟子及一菩薩,並從屬擔負寶蓋的二飛天。蓋家店出土的佛板底座遺失,雕刻手法較為粗糙,圖像刻花比較樸拙,與本佛板無法比肩。
此銅佛板的文化價值非同尋常,在數量有限的遼代佛教單體造像中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地位。佛板內容關聯北朝至遼代數百年間的佛造像史,匯聚不同時期和諸多地域文化因素於一身。而且通常所見具有官方性質的遼代佛教造像,多表述了密教和華嚴思想,此佛板則反映了阿彌陀佛所代表的西方淨土信仰,對於研究遼宋時期的佛教信仰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閲:唐彩蘭編著《遼上京文物擷英》圖版27,呼和浩特 遠方出版社,2005年。